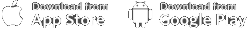韩公本意筑三城,拟绝天骄拔汉旌。
岂谓尽烦回纥马,翻然远救朔方兵。
胡来不觉潼关隘,龙起犹闻晋水清。
独使至尊忧社稷,诸君何以答升平?
【赏析】:
《诸将五首》是一组政治抒情诗,唐代宗大历元年(766)作于夔州。这里选的是其中第二首。当时安史之乱虽已平定,但边患却未根除,诗人痛感朝廷将帅平庸无能,故作诗以讽。正是由于这样的命意,五首都以议论为诗。在律诗中发绝大议论,是杜甫之所长,而《诸将》表现尤为突出。施议论于律体,有两重困难,一是议论费词,容易破坏诗的凝炼;二是议论主理,容易破坏诗的抒情性。而这两点都被作者解决得十分妥善。
题意在“诸将”,诗却并不从这里说起,而先引述前贤事迹。“韩公”,即历事则天、中宗朝以功封韩国公的名将张仁愿。最初,朔方军与突厥以黄河为界,神龙三年(707),朔方军总管沙吒忠义为突厥所败,中宗诏张仁愿摄御史大夫代之。仁愿乘突厥之虚夺漠南之地,于河北筑三“受降城”,首尾相应,以绝突厥南侵之路。自此突厥不敢逾山牧马,朔方遂安。首联揭出“筑三城”这一壮举及意图,别有用意。将制止外族入侵写成“拟绝天骄(匈奴自称”天之骄子“,见《汉书》)拔汉旌”,就把冷冰冰的叙述化作激奋人心的图画,赞美之情洋溢纸上。不说“已绝”而谓之“拟绝”,一个“拟”字颇有意味,这犹如说韩公此举非一时应急,乃百年大计,有待来者继承。因而首联实为“对面生情”,明说韩公而暗着意于“诸将”。
颔联即紧承此意,笔锋一转,落到“诸将”方面来。肃宗时朔方军收京,败吐蕃,皆借助回纥骑兵,所以说“尽烦回纥”。而回纥出兵,本为另有企图,至永泰元年(765),便毁盟联合吐蕃入寇。这里追述肃宗朝借兵事,意在指出祸患的原由在于诸将当年无远见,因循求助,为下句斥其而今庸懦无能、不能制外患张本。专提朔方兵,则照应韩公事,通过两联今昔对照,不著议论而褒贬自明。这里,一方面是化议论为叙事,具体形象;一方面以“岂谓”、“翻然”等字勾勒,带着强烈不满的感情色彩,胜过许多议论,达到了含蓄、凝炼的要求。
“尽烦回纥马”的失计,养痈遗患,五句即申此意。安禄山叛乱,潼关曾失守;后来回纥、吐蕃为仆固怀恩所诱连兵入寇。“胡来不觉潼关隘”实兼而言之。潼关非不险隘,而今不觉其险隘,正是讥诮诸将无人,亦是以叙代议,言少意多。
六句突然又从“诸将”宕开一笔,写到代宗。龙起晋水云云,是以唐高祖起兵晋阳譬喻,赞扬代宗复兴唐室。传说高祖师次龙门,代水清;而至德二载(757)七月,岚州合关河清,九月广平王(即后来的代宗)收西京。事有相类,所以引譬。初收京师时,广平王曾亲拜回纥马前,祈免剽掠。下句“忧社稷”三字,着落在此。六句引入代宗,七句又言“独使至尊忧社稷”,这是又一次从“对面生情”,运用对照手法,暴露“诸将”的无用。一个“独”字,意味尤长。盖收京之后,国家危机远未消除,诸将居然坐享“升平”,而“至尊”则独自食不甘味(至少诗人认为是这样),言下之意实深,如发出来便是堂堂正正一篇忠愤填膺的文章。然而诗人不正面下一字,只冷冷反诘道:“诸君何以答升平?”戛然而止,却“含蓄可思”。这里“诸君”一喝,语意冷峭,简劲有力。
对于七律这种抒情诗体,“总贵不烦而至”(《诗镜总论》)。而作者能融议论于叙事,两次运用对照手法,耐人玩味,正做到“不烦而至”。又通过惊叹(“岂谓”二句)、反诘(“独使”二句)语气,为全篇增添感情色彩。议论叙事夹情韵以行,便绝无“伤体”(伤抒情诗之体)之嫌。在遣词造句上,“本意”、“拟绝”、“岂谓”、“翻然”、“不觉”、“犹闻”、“独使”、“何以”等字前后呼应,使全篇意脉流贯,流畅中又具转折顿宕,所谓“纵横出没中,复含酝藉微远之致”(《说诗晬语》),也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。